不合時宜的半生-2012年登在台大土木系電子報的文章另類學習與職場生涯高銘堂
前泛亞工程建設公司 總經理
臺大土木系B60級校友 |
 |
| 與前榮工處處長曾元一學長(台大土木48,左);榮民工程公司前董事長劉萬寧學長(台大土木54,右)合影 |
早期的學習
我初中念台中一中時,因自由的學風,讓我常去找一些和正課與升學無關的東西看,圖書館、書局、舊書攤乃至某些有心的老師處,常有意外的收穫。許多的「發現」回想起來雖是粗淺、片段的,但對比當時一元化思想環境的虛偽與粗糙,讓我對體制產生強烈的反感。在那種充滿窒息感的氣氛中,尋求些微改變都是不可能,結果你只會憎惡自己的懦弱、無能,甚至自暴自棄,懷疑個人存在的價值;因此我常自嘲自己或是普希金筆下「多餘的人」,對社會不能有什麼幫助。所以這是一段矛盾的日子–知識帶來喜悅,也帶來挫折與煩惱–但也因心中常存憤怒與鬱悶,我對理性、智性的追求總是保持阿Q般的執著,態度決定命運,影響我往後的學習與職業生涯。
到了高中,我學了圍棋,沉迷於變幻萬千的棋局中;開始是假日,晚上,後來也不太去上課了,整日流連棋社,在與來自社會各階層棋友的互動中也得到很大的樂趣。玩物喪志的結果使我更疏離正規教育,中一中換了個重視升學的校長後,種種的約束激發了我的叛逆,又以血氣方剛,在最後的一年我與老師、教官發生了不少的衝突,至今仍不堪回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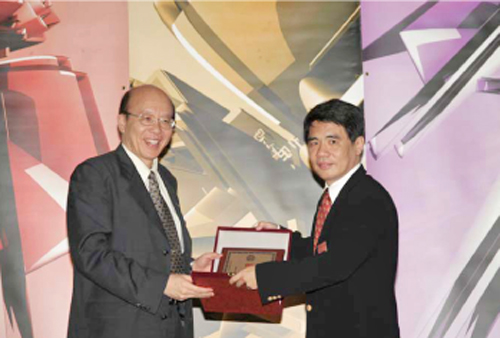 |
| 2006獲頒本系傑出校友獎 |
台大的日子
經歷了一些波折,我還是進了台大;然對好好的坐在課堂聽課這件事不但做不到,而且每下愈況;本來對之還有點興趣的東西,一旦進了教科書,我就覺得厭煩。這種負面的情緒一直困擾著我,畢業時我借用哈姆雷特裡的「will have no more marriages」, 在紀念冊寫了「再也沒有畢業了」的留言,招認自己不適合正規教育;多年後服務的單位數度要保送我出國進修,我也忠於以上說的留言而婉拒了。但回想這只求60分的三、四年,我的學習態度還不算很頑劣。比如說,考試前一天,甚至近午夜時才拿到全新的原文教科書,我還是會從Preface看起,先去了解這門課講的是什麼?著者要我們注意些什麼?有什麼進階或相關的科目?不把這些弄清楚,我連公式都背不下去。這種堅持不先見「林」,就不去見「樹」的思考習慣,讓我對各專業科目留有大致的輪廓;所以後來我與許多國內、外工程專家、學者一同面對複雜的技術問題時,能很快的在理論與實務間找出平衡點,並作出最後的決定。
大學四年除了下圍棋、打橋牌打發時間外,我還勤於找禁書。中文的除了被警總禁絕外,勉強出版的也會有被塗黑的情形,只能用反面解讀或以偏概全的辦法來猜測真相。但英文的倒有不少漏網之魚,像大四時我在研究圖書館一個堆滿舊書報的房間,找到了20到50年代的TIME雜誌,於是帶了一本字典,將近一個禮拜把幾大捆雜誌裡有關中國、蘇聯、台灣、共產主義相關的文章囫圇吞棗,猶是意有未盡。比較可惜的是找到些硬裡子的書,那時多少可以看懂些,但疏懶再加上精力都在棋橋上,以致登堂而未入室;現成了花甲衰翁,想看也看不懂了!所以勸大家要「惜取少年時」,台大人的頭腦是有資格在學問知識上要多一點的。
大學四年除了下圍棋、打橋牌打發時間外,我還勤於找禁書。中文的除了被警總禁絕外,勉強出版的也會有被塗黑的情形,只能用反面解讀或以偏概全的辦法來猜測真相。但英文的倒有不少漏網之魚,像大四時我在研究圖書館一個堆滿舊書報的房間,找到了20到50年代的TIME雜誌,於是帶了一本字典,將近一個禮拜把幾大捆雜誌裡有關中國、蘇聯、台灣、共產主義相關的文章囫圇吞棗,猶是意有未盡。比較可惜的是找到些硬裡子的書,那時多少可以看懂些,但疏懶再加上精力都在棋橋上,以致登堂而未入室;現成了花甲衰翁,想看也看不懂了!所以勸大家要「惜取少年時」,台大人的頭腦是有資格在學問知識上要多一點的。
土木系的師長並不苛求,讓我能順利畢業;到了職場才知道,頂著台大土木系的光環,少有人懷疑你專業上竟無根底,所以除了慚愧外,我對母系非常感恩。另一方面我們台大無形的自由學風與有形的圖書資產讓我累聚豐富的「常識」以及英文實力,一輩子受用不盡,念其他的大學不可能有此際遇的。
 |
| 2009赴馬爾地夫出席亞太營造商聯合會理事會,與大會會長陳煌銘學長 (台大土木56,右)、秘書長郭倍宏學長(台大土木62,左)合影 |
海外工程
預官退伍後,我想到中東以時間換美金,就進了榮工處海外部等候派遣出國。但主管觀察了我一、兩天後就告訴我,我的英文閱讀能力比許多留美多年的同事還好,我自己也很訝異;因我從無出國深造的念頭,總以為那些托福考高分的同學們英文應比我強太多。多年後看了些語文專家寫的如何把外文念好的文章,才知我大學及當兵時為了解惑、求知,狂熱的看英文雜誌、圖書,只想理解文章內容,不背單字,沒有把英文搞好的壓力,反而是最有效的學習方式。因為這樣我就留在海外部將近十年,主要工作是閱讀標書及合約、寫施工計畫、研究工法、估算成本、準備標單、到國外勘察工地,與業主、代理或當地的合作廠商溝通等;不久後更參與較上層的業務談判工作,受命與先進國家工程公司、重工業、或大商社等洽談大工程的共同投標。那時台灣工程界涉外人才不多,而我入行未久,就面對幾千萬、幾億美金的數字,開始時覺得有點像是在扮先鋒廖化,有點壓力。但多年穿梭歷史時空所累積的膽識,很快的幫我融入歐、美、日等先進國家所建立的商業體系。克服短暫的羞澀,撐過許多場面後,也交了不少外國朋友,後來到了泛亞公司要引進先進施工方法或海外資源時,有好幾位都幫了我的忙。
有好幾年,我每個月都要出國,經驗累積後,對國際工程談判更有信心。但我對知識及許多的真相好奇心絲毫未減,除了上飛機就埋首於在國內仍受管制的報章雜誌;到了任何過境航站或城市,看到書店就進去翻找,有「好書」就帶回旅館,或在回程的飛機上看,有些看了一半,入境前只好丟了。所以思想方面,我可能比一般人早了十年解嚴,也因此感慨我們這個世代,許多習慣了戒嚴而不太質疑權威的好人才如果能早些與國際連結,台灣的社會一定比現在活潑、進步。所以廿餘年來,我在泛亞約談新人,總要問他們有沒有看課外書或雜誌,得到的回答往往是有,但幾乎都是理財、電腦軟體或勵志類等對事業或賺錢明顯可以加分的東西。多年來只有一位我們台大土木系的同學告訴我,他看了許多文、史、哲方面的書;經長期的觀察,他在公司的表現真的比別人好,尤其在參悟人性深邃處,更是可圈可點。看課外書與職場表現有什麼因果關係,我不敢說;但應該多看書,而且看的書不必太功利導向吧?
 |
| 參加本系東南亞工程教育訪問團,與師長、系友,2004在吉隆坡合影(右二) |
國內工程
1980年代後期,榮工在海外方面減量經營,重心轉到規畫六年國建的國內市場。我也順勢轉到了泛亞公司,開始接觸國內工程。泛亞是榮工、退輔會、中鼎公司以及幾家水泥公司的合資企業,但資本只有一億元左右,要承攬國際級的大工程條件實在有點不足。但那時國內由台北捷運起,開始引進如英文合約,施工網圖、施工圖及計畫送審等外國工程管理制度,我和幾位國外部同事可是駕輕就熟。而且有些大工程招標時,業主要求外國廠商參與合作,我們也很容易的找到日本、歐洲的老朋友們幫忙,所以業務很快的獲得突破。廿餘年來,我們承攬的工程是國家重大建設,競爭對手是資本額比我們大好幾倍的上市、櫃工程公司。我們作法多少與別人不同,比如說,在同樣規模工程,用的工程師及參謀比同業多出50~100%;同業認為發包較有效率,我們卻自擁施工機具,雇用領班、技術工等參與施工;財務上不作任何業外投資,亦不向銀行融資貸款。經營的結果是資本額憑歷年盈餘由一億餘增加到十億餘,同時現金股利也發了二十幾億元,在營造業甚或公營公司中算是個異數。也因此確信在過度競爭的營造業,保守、傳統的經營方法還可存活、成長。公司現仍健全茁壯,在慶幸中,我選擇提前交棒,讓年輕人有機會能面對新的變局。
營建業是非常「在地化」與「個人化」的行業,一方面習慣事必躬親的老闆們常為無法掌控所有事態的發展懊惱;另一方面他們因勞資成見,卻不願授權駐地員工在第一時間去處理與各方人士的問題。在互不信任下,主從關係很容易成了草芥寇讎,工地管理那能不出大問題?公司的制度設計要學習國際知名公司,寫得盡善盡美很容易;但如何讓員工們像80年代前的日本會社員,隨時都可為公司拼命、犧牲,卻是個難題。再仔細一想,這個亂度很高的行業比的是哪個競爭者犯的錯誤較少,較不致命-比如說工地與第三者發生糾紛,員工馬上能為公司挺身而出,小問題不會擴大到不可收拾,才能談到賺賠。所以一開始我就重視公司文化與風氣更甚於典章制度,尤其不能讓員工把它當成天塌下來,總有別人頂著的國營企業。
我曾看過一些社會學與政治學的理論,因之不否認公司組織是一群人自私地追求個人最高滿足之所在;但為保障參與者的某些權利這共同體也需有合作、道德、和是非等觀念形成的潛規則,來壓抑內部競爭可能引發的敵對行為。而公司的領導者就是決定團體中「誰得何物又為何(who get what, and why)」的利益分配者,必須善用酬勞、地位、特權與榮譽等資源來消弭成員間矛盾並積聚戰鬥力。但在資源有限,不能平等又需考慮平等的情況下,我不得不訴諸某些形而上的激勵手段,如宣揚利他精神(altruism),或團體自我犧牲(partisan self sacrifice)的概念,總算也建立了一個至少成員都能遵守所謂實用道德(pragmatic morality)的小團體;也因有高度的凝聚力,這個公司採用的某些經營、管理辦法,如前面所說,可以跳脫行業的窠臼。但時日一久,公司文化有無異化的現象?團體內有沒有形成派系及特定階級的趨勢?卻成為我很大的負擔。也因此覺悟到我理想的工程烏托邦只能在很小的範圍實行。我個人也以「年六十餘,所更非一」,個性由頑強趨於溫和,思想亦由相信「善良意志」的理性主義轉變為尊崇個人價值的自由主義。
 |
| 同學聚餐(台大土木60),前排右一,2012七月 |
對學弟、妹的期待
我對權力、榮譽、利益等支配個人行為與衝動的基本慾望,如何影響我與周遭的人們,會很積極的去探究,並作最快的自我調整;而大多數的知識分子卻把這樣的政治敏感等同於汲汲營營,這是不對的。因作為社會精英,要實踐自我與理想,就必需取得相稱的權力,包括可以支配他人的強制性權利,也就是權威(authority);必要時也可以運用個人的資源和權力去塑造一種社會情境來影響別人的觀感,使他們的行為順從我們的意願,這就是影響力。許多認為自己有真才實學,不屑去爭取權威和影響力的好人,最後連保持獨善其身的餘裕都要失去;這樣子的自反而縮不是美德,人生不能避免權力競合和政治鬥爭,不可沽名學「名士」!
土木工程學的英文是Civil Engineering,顧名思義就是市民、公民之事,比起工學院其他學系而言,我們的系友,更有機會當部長或居高位,服務公眾。但現實與歷史顯示許多在學術上有名譽者,一旦掌權,常因理念過於清晰,而會爆出「正義的火氣」,一發不可收拾,很可能傷害到他們想幫忙的人。所以我借南宋呂祖謙(東萊博議的作者)所說的「善未易明,理未易察」,給各位未來主人翁參考;胡適當校長時,也以這八個字敦告北大學生:「世上事務,常有多面性,須瞭解問題,多方思考,不宜在資訊不足,瞭解不深下,妄作判斷」。我們服務於工商界的校友們如犯了專斷、武斷的錯誤,個人或家庭要付出極大的代價;但主導公共事務的政界人物如擇善固執,卻是社會大眾幫他們付出代價,這是很不公平的。所以身為秀異份子的我們,如真有鴻鵠之志,是不是要效法東萊先生任官做事,時時「反求諸己」、「反觀內省」,絕不用「時異事殊」作失敗時的藉口?
我從年輕起,雖有心求真、求善,然限於資質、個性,成就不大;但看盡社會百態後,常感慨如果每個人在出社會後都要受夠折磨才能知天命,那麼曾歷滄桑的前人還是應把所體驗過的無情世道,無常世事勇敢講出來,讓後輩知道「成長」應付的代價。而另一方面,我也知道許多台大人有瀟灑過日子的條件,不認為自己要知道那麼多,但君子不一定可以長久遠庖廚的,相對於大多數的系友,我這些很另類的職場生涯記事與愚人之得,還是可以讓大家當參考吧?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